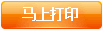首页 > 科教之家 科教动态
七旬教授夫妻同台授课20年获赞 曾被学生叫老虎
2014年11月13日 18:56
直到今天,年过古稀的吴老师和黄老师还对自己的突然走红感到非常困惑。
在他们看来,和老伴儿一起上课,是一件多么自然而然的事。从1994年第一次一同走上讲台开始,中科院吴乃虎教授和北大生命科学院黄美娟副教授两个人的课堂在全国20多所高校流转,已经持续了整整20年。
中科院研究生杨晗还记得第一次上“基因工程原理”课的情形:讲台上有两位老师,哪一位是吴乃虎?她一时有点懵。上课铃响,男老师清清嗓子开始讲课,女老师就坐在讲台的另一侧。
一上课,吴乃虎就像中了一种魔法,关键处兴起时,一回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笃笃地写。常常是讲完一个知识点,板书也正好写了一个黑板。
趁他还在黑板前“高谈阔论”时,黄美娟就默默走上前替他擦黑板。有同学想上去帮忙擦,黄老师打个手势制止,小声说:“好好听课。”
有时,吴乃虎上课讲着讲着就讲起他的青年时代,然后突然打住了,他瞟一眼老伴儿,说:“你们看,黄老师又看我了,说我跑题。”
吴乃虎讲错了细节,黄美娟会在一旁轻声提醒;吴乃虎有没讲太明白的地方,黄美娟会直接站起来补充。这时的吴乃虎就站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
2007年上过课的胡文清感叹:“吴老师和黄老师的课堂成了一个景观。”
上完一个学期的课程,杨晗在日志中写下:“一对年过七旬的老教授夫妻同台授课,他们举手投足体现出的和谐和默契不知道羡煞了多少青年学生。”
可他们觉得这太正常了。就像在家里准备开始跟访客聊聊之前,黄美娟给吴乃虎拿来橘子和脆枣,吴乃虎把盛满热水的保温杯放在黄美娟的面前。
今年,吴乃虎的课堂是周三晚上6点半在中科院能容纳2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中开设。如果你踩着时间去,那多半只能站着听课了。多年来,无论大小教室,只要是吴乃虎的课,总是场场爆满。一位有座位的学生说:“中午就来占座位了!”
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基因工程原理”6个字,就会出现“吴乃虎”的名字。他写的经典教材《基因工程原理》1989出版以来印刷17次。而他印过两套名片,一共200张,连一半都没用完。
“目前,国内年龄在55岁以下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绝大多数科研及教学人员都读过这本书,其中有很多人还听过我们的课。” 吴乃虎讲得信心满满。
现在在课堂上,看着学生不好好上课,吴乃虎批评在嘴上,疼在心里。想及当年自己的艰辛,他就替现在的学生着急: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年轻,怎么能不好好学习呢?
1983年初,吴乃虎谢绝了美国纽约凯瑟琳肿瘤研究中心年薪2.5万美元的邀请,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生化分子生物学系学习。他说:“我留学是服从国家的需要,真正学习新东西,而不是为了赚钱。”他拜在世界著名分子遗传学教授吴瑞门下,开始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
当时已是45岁的吴乃虎,几乎是从头学起。无论是英语水平、实验技能和专业知识都很差,大多数试验在国内都没做过。3年里,他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1年后,康奈尔大学主动将吴乃虎的身份从访问学者转为博士后。
1986年回国后的第二天,吴乃虎便兴冲冲地回所里报到,希望尽快开展实验。没想到的是,所里分子生物学方面几乎一片空白。
别提实验室和经费,连一个像样的放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他就在别人实验室的通风橱边上放了一个三屉桌。也就在那张小桌上,他写完了《基因工程原理》。
直到现在上他手到擒来的“基因工程原理”课,吴乃虎还是要在上课的前一天搜集最新资料。然后由黄美娟组织整个的课程顺序,确定讲课内容的详略。
在吴乃虎的书柜最下层,有十几册统一用黑色文件夹装订好的笔记和资料,每一册都有五六厘米厚。他细心珍藏了20多年。
这是他从美国带回资料的不到十分之一。在美国时,他就开始酝酿要写这样一本“让国内的学子能够迅速地掌握基因工程的理论知识”的书。
吴乃虎说:“没有黄老师多年的支持与关心,这本书我写不出来。”
说罢,他翻箱倒柜从书桌柜子里捧出一大摞的资料,这是新书《分子遗传学原理》第一章修订全过程的所有材料。一共9本,两度更改名字和结构,几乎每一本的每一页,都有吴乃虎和黄美娟的笔迹。红色、蓝色、黑色,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不同的修订处,工工整整,每一处修订都用了规范的修订符号。
每次上课,他们都会提前大约一个小时到教室,黄老师整理讲义,吴老师就跟学生聊天,或者“突然袭击”检查笔记。
黄美娟每学期与吴乃虎一起上课,做笔记比学生都认真。单手边能拿出来的就有11本。起初,重点标的多,到后来,她更多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笔记正文下方。每一节课后,她都会拿着本子跟吴乃虎说:“吴老师,你看啊,这里没讲到,那里还需要加强。”
访客想多跟黄美娟聊聊,可她总是说:“你们聊,你们聊。”到自己的书房,给访客准备相关材料。在吴乃虎讲起什么又刹不住时,黄美娟就喊一声:“吴老师,不要再讲这些了,讲重点!”
吴乃虎讲课强调概念的准确。比如这些年他一直在纠正学生对“同源性”这个概念的错误认知。很多教材上讲两个基因有90%的同源性。他说,同源性就是实实在在指来自同一个“祖宗”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你能说你和你姐姐有90%的同源性吗?同源性就一句话,yes or no。”后来无论什么场合他只要碰到这个问题就会讲,现在学界逐步地改了过来。
教书27年,吴乃虎说自己从没迟到早退过一次,赶不上吃晚饭也要先去上课,趁着课间躲到黑板后面吃一点东西。
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不准上课时接听手机,不让交头接耳,也不许迟到早退。有学生私下里叫他“吴老虎”,他一听“哈哈哈”地笑了。讲课3小时后,吴乃虎也不觉得累,还一一解答学生提问。
1994年的一天,吴乃虎上完课已经晚上9点半,可直到11点,学生打来电话说,问问题的同学太多了,吴老师还在讲解。黄美娟知道不妙,果然,吴乃虎很快因为心脏漏跳躺在了医院。从此,黄美娟就每次课必同吴乃虎一起去。
“吴老师板书手劲极大。”黄美娟说,“给他擦黑板,我都当锻炼身体了。”1996年退休后,为了让吴乃虎潜心写书上课,黄美娟还自学了电脑技术,全心协助吴乃虎。
当黄美娟受邀讲学时,吴乃虎也会坐在讲台的一侧,给老伴儿擦黑板,提醒老伴儿时间。吴乃虎常常感叹:“你说黄老师这个人也奇怪。工资不在乎,书上的署名也不要。”后来,再出版《基因工程术语》和《分子遗传学原理》时,吴乃虎执意要把黄美娟的名字写上去。
中科院研究生王青回忆,讲台上的两位老师都白发苍苍,吴老先生在众多学生面前回忆起他们的第一次相遇,说,“我那时候就知道你们师母是个好姑娘,是要和她过一辈子的。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谈恋爱朝三暮四,是找不到对象的!”
问起跟老伴儿的相识,吴乃虎嘿嘿笑了没有说话,看了看窗外,又嘿嘿笑了,说:“我相信一见钟情。”他回忆给心上人写信,第一次写“黄美娟同志”,第二次写“美娟同志”,到第三次就直接写上了“美娟”。不过一辈子也从来没有叫过“亲爱的美娟”,他说:“亲爱不亲爱心里自然明白的嘛。”
课间,总有学生请老师给教科书签名,吴乃虎常常在上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头,下册就必定是先写个逗号再写自己的名字,把前面的位置留给黄老师。
吴乃虎想起文革时疾风暴雨,一夜之间满楼都写满批判自己的大字报,黄美娟直接说:“我原来还想等两年再结婚,现在看来,结!”新郎官的衣服都是黄美娟买的。吴乃虎说:“是黄美娟娶了吴乃虎。”
现在上课,两人分工明确。吴乃虎负责收集资料,跟进科学前沿,改进课程内容。黄美娟负责布局授课内容,查漏补缺,组织复习课,出所有的考题和标准答案,最后批改考卷。
吴乃虎小声说:“她跟我商量考题啊,我也不能直接说,咦,这个不要!听了这么多年课,改了这么多次考卷,她现在也是基因工程专家哩!”
2004年从中科院退休之后,吴乃虎把主要的精力都倾注在教学中,讲台成了他生命的主要舞台,用他的话说,这是“最后的用武之地”。
他退休后,北京某高校曾高薪聘请他。不多久就这一派找他,那一派找他。吴乃虎觉得自己是来教课的,不是来掺和这些的!他说:“我恨透了这些人事问题。”
1964年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吴乃虎被分配到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文革中他被打倒,被批斗,但他有自己的原则:不低头、不瞎说、不害人、不参加任何运动,有机会就读书。住在北郊亚运村附近,他一有机会背着一本英语字典,骑车两小时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数十本的笔记,到现在还都整整齐齐地码在家里的储物室中。
在科研与荣誉上,吴乃虎说自己看得很开:“我已经到顶了,至于更高的头衔,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不够。通过邪门歪道去当,我不干。”
吴乃虎上课,常常是学生越鼓掌,他越起劲。黄美娟补充:“他第二天还激动呢。” 学生杨晗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他的授课情景,那分激情,那分投入,那分陶醉,他对所讲知识的,那种信手拈来,足以激起我们对科学的崇拜。”
吴乃虎也曾在课堂上声音爽朗地开玩笑:“再蹦跶几年,我就搬到八宝山去啦。”
而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挪着细碎的步子带着记者翻看一屋子书和笔记,摇摇头,自言自语:“我一辈子看了这么多书,学了这么多东西,都想讲。课太少,身体也不行了,想讲,讲不完。”
吴乃虎第一次讲授“基因工程原理”,是在1989年。如今,记者采访到的一些不同年级的吴乃虎和黄美娟的学生,都会回忆起学期末最后一次课的情形:
“下课铃响,几百人的阶梯教室,没有一个人动。老夫妇擦了黑板,收拾好讲义,挎上背包,挥手走出教室。全体同学自觉起立,掌声可以持续好几分钟。” 赵雅娇
责任编辑:wb001
文章来源:http://edu.72177.com/2014/1113/18868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