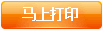首页 > 科教之家 科教动态
“学霸”少年9岁办独奏音乐会 蝶泳夺全国冠军
2014年11月13日 18:24
刘泽锴在音乐会上

刘泽锴和好朋友小元
世界上有两个刘泽锴。
一个是所谓“天才”,另一个则是一名13岁的男孩。
前者生活在人们的目光和传闻中,开独奏音乐会,摘全国游泳大赛金牌,还老是考班上第一名。
后者则生活在深圳蛇口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讨厌语文课本,热爱巧克力饼干,害怕老爸的威严。
世界上并没有两个刘泽锴。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这个少年晃晃悠悠地走出“小托福”考场。
如果成绩合格,他将拥有就读美国高中的语言资格。为此他准备了好几个月。
他已经收到来自美国两所顶尖艺术高中的面试通知。此时,距离他开始学习钢琴,整整10年。
“我才不是什么天才!”刘泽锴仰着一张圆鼓鼓的脸说。
他只是比别的孩子忙
这是一双宽大灵敏的手。张开手掌,大拇指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能达到25厘米,在钢琴键盘上跨越12个白键,快起来一秒钟能弹奏十几个音符。
这也是一双极为有力的手。在泳池里入水、划水、出水,能带动身体行进五六千米。
13岁的刘泽锴是这双手的主人。这个练习了10年钢琴和8年游泳的少年,用这双手赢取了不少奖牌、奖状和掌声。但他对它们的感情有点儿复杂。
“我从小就不能打篮球,也不能骑车,你应该明白。”他摊开手掌,目光扫过十指说,“因为它们不能受伤。”
在他六七平方米大的琴房兼书房里,十几枚黄色、白色、褐色的奖牌被随意地扎成两束,飘带捆起来塞进书架缝隙中。里面既有深圳南山区儿童游泳比赛一等奖,也有美国西雅图国际钢琴赛最佳演奏奖。
还有几块看起来是随手丢在书桌和杂物堆里的金灿灿的牌子,连包装都没拆过。
“我从来不看。”刘泽锴伸手拨弄着它们,嘟囔道,“占地方。”他家的玄关、客厅里到处都有奖杯,母亲陈喆更是懒得抬眼,挥了挥手说:“还有奖状,一箱子呢。”
所有这些奖的背后是刘泽锴真实的生活。这生活被学业、游泳、钢琴几乎完全填满。眼下升至初二,游泳渐渐被放下,取而代之的,用男孩一本正经的话说,是“无休止地练琴写作业”。
尽管被特批不用参加早读,但每天早晨他还是在上学路上吃早饭。中午的午休时间,他趴在课桌上埋着脑袋赶作业,以便为晚上练琴腾出时间。周四周五,他下午不上课,直接回家练琴。周末,他要去香港演艺学校上“大师课”,还得补习粤语。
这个小男孩从未拥有一个叫做“天才”的“身份”,他只是比别的孩子忙,忙成了其他父母用来教育自家小孩的——“别人家的孩子”。
仅9岁这一年,他就举办独奏音乐会,摘得全国少儿游泳分龄赛蝶泳冠军,并获得美国第四届西雅图国际钢琴赛金奖。几年来,他音乐会不断,著名钢琴家郎朗多次邀请他同台演奏。他还签约了经纪公司,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录制电视节目。如今,亚洲顶尖钢琴教育家黄懿伦亲自为他授课,美国最好的艺术高中因特劳肯向他敞开大门。
在最近的一次英语考试中,他的成绩位列班级第一。事实上,他的数学、物理成绩也一样拔尖,外号“学霸”。
游泳教练评价他:勤奋、不娇气、不顶撞、不偷懒,呛水从来不哭。
班主任评价他:主动,有悟性、好奇心,注意力特别集中。
经纪公司老板评价他: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全面。
“和别的小朋友相比,他的‘业余时间’太少了。但他的快乐也许也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可能更成人化。”游泳教练冯杰说,“别的小孩打游戏、看漫画、玩沙子很快乐,他获得荣誉也很快乐。”
2013年5月,刘泽锴开了一场慈善音乐会,为此他用了两个月时间准备曲目,集中练习。事实上,在3月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曾试图反抗过。
“你没搞错吧?太累了!”
“我是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母亲答道。
明年2月,经纪公司为刘泽锴筹备的又一场音乐会将在鼓浪屿举办。在这场音乐会上,这个13岁少年的身份,将是“全球杰出华人少年演奏家”。
“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样”
陈喆自称对儿子从来没有“期望”。
2001年5月,即将临盆的准妈妈陈喆还在弹钢琴和古筝。从湖北老家到深圳“淘金”之前,她的专业是音乐教育。尽管改行做了企业管理,但她仍在工作之余开班教琴。
刘泽锴是5月的最后一天出生的,剖腹产,7斤半。陈喆竭力强调自己并没有多么重视这个孩子,“生下他之后,我听见婴儿哭声,还问,是谁家的?”
没出满月,她又恢复带课。
“我对他没什么设想,都没怎么管!”陈喆说。但只要谈到儿子,她马上又有讲不完的传奇。在她的描述中,小时候的刘泽锴就与众不同,他不挑食,不爱哭,不认生,“乖得让人感觉有问题”。
在母亲的回忆中,刘泽锴刚1岁大时就很有乐感。电视上播放踢踏舞表演,“他跺脚、眼神都合得上节奏”。
不管是不是真的天赋过人,刘泽锴的生命注定与钢琴相连。母亲陈喆曾获第三届香港国际钢琴邀请赛“英才导师”,带过的学生钢琴十级通过率是100%。
这位当音乐教师的母亲说:“最初,钢琴不过是给他的一个玩具。”
陈喆记得很清楚,儿子3岁开始学琴,要手脚并用,才能爬到琴凳上。第一首完整弹奏的曲目是基本由哆来咪构成的《轻轻地划》。
为了让刘泽锴在琴凳上坐住,她买来儿子喜欢的糖果或黄豆。弹完一遍练习曲,就给一颗。
“这么大一袋黄豆!”刘泽锴动作夸张地比画着,“不知道弹了多少遍才吃完。”
四五岁时,他一天能在琴凳上坐半个多小时。6岁以后,这个数字变成了一天7到8个小时。
钢琴成了他童年唯一的玩伴儿。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他练琴练到“从来没下楼玩儿过”,小区的孩子都不认识他。
“小时候我真的以为那是玩具。”如今也不过13岁的刘泽锴回忆道,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玩具玩儿起来那么累,但还是说服自己,把曲子当成电子游戏,一首首打通关。
“没有一个学生比我的孩子更勤奋。”陈喆骄傲极了。
在深圳蛇口一幢普通的住宅顶楼,刘泽锴的琴房位于贴边临街的房间,这样琴声就不会打扰邻居。
乐谱和音乐CD塞满了这间小屋的书柜,从桌面一直堆到屋顶。“来套最累的!”刘泽锴搬来凳子,爬上去,踮脚从上层抽出一本琴谱。
他翻看了一会儿,把它端放于琴键上方的谱架,抬起手,沉默了片刻,又落下手。
《黄河组曲》雄浑的乐声立即填满了整个房间。
弹琴的人长着一张胖嘟嘟的圆脸,穿着浅蓝的夏制短袖短裤校服,赤脚踩着踏板。在严肃壮丽的音乐氛围中,他并没有皱眉头,但也没有微笑,而露出非常坚定冷静的神情。伴随着手指的起落,眼睛时开时闭。乐句悠扬时,他随之摆首;乐句沉重时,他跟着弯腰。一个13岁的男孩,在“黄河”的“巨浪”中,翻腾自若。
一曲终了。几乎一瞬间之后,天真的笑容就爬上了那张圆脸,烂漫的神情也充满那双大大的眼睛。
“我能理解这里面的情绪!”他认真地说。他最喜欢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和巴伦博伊姆的演奏,也喜欢挑战李斯特公认的“高难度”曲目和世界上最快的钢琴曲之一《野蜂飞舞》。
小时候他弹《庆翻身》,会听到“哥哥姐姐在里面跳舞”;如今他演奏《钟声》,会边弹边凝神说:“你听,那个声音从很远的地方来。”
“刘泽锴不能没有钢琴。”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说。
三四岁时,他爬上琴凳,脚丫子还够不着踏板。再看眼前,刘泽锴的肩膀早就比母亲宽了。尽管脸上还带着稚气,但他的声音已经变得像个大人。
“你还吃,长胖!”“作业写完了吗?”“你一个星期没练琴。”晚饭快要结束的时候,陈喆语速极快,不停唠叨着。
即使是在吃饭、聊天或任何一个日常的片段里,她都不放弃向儿子摆事实、讲道理的机会。
在电梯里遇到邻居,“见人要主动打招呼!”听到别人的观点,“要先表示认可,再说你自己的看法!”记者上门采访,“要学习这种大方、勇敢去沟通的精神”……
“我一句话没说,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刘泽锴一点儿也不恼,而是笑嘻嘻地调侃母亲。
晚饭后,陈喆下楼跑步。电梯里有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推着小单车,嘻嘻哈哈地打闹尖叫。
这位母亲脸上浮现出高傲的神情说:“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样!”
今年1月,刘泽锴去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那天天气有点冷,他裹上妈妈的大棉衣,背上自己的西装皮鞋,一个人出了门。
“我没垮,孩子也没垮”
“7岁之后,我介入得比较多。他弹的每一首曲子,都是我陪过来的。”刘泽锴的父亲刘大海说。
他曾是中国向海地派遣的第二支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儿子小时候,他在家的时间并不多。
“父母对孩子应该少讲教育,多讲陪伴。”在刘泽锴开始接受更为专业的钢琴训练之后,刘大海的维和任务也结束了,成为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
每节钢琴、乐理课他都陪儿子一起上,并抱着一个大本子,详细记录课堂内容。
刘泽锴找出一本和杂志差不多大却足有几百页的笔记来。上面密密麻麻手写着日期、科目、曲目、课堂内容,并用严谨的分级目录隔开。有的页面上甚至还有简谱写成的乐章要点。
在这份笔记的结尾处,标识着“第104周”。
“这本写了两年多,一堂课不差,我没垮,孩子也没垮。”刘大海说。上完课回到家,刘泽锴练琴的时候,父亲会根据笔记的内容,随时作出提示和指导。
几年陪课下来,刘大海的手指头虽然不会弹琴,但脑袋里,对钢琴和乐理已经非常精通。有闲暇的时候,他还能带带乐理课。
“每周固定那两天,再重要的应酬他也不会去。”刘大海的一个朋友表示。在他看来,作为父亲,刘大海很严厉,“小孩弹错一个音符,要重新弹两遍”。
“他说爸爸会点穴!”刘泽锴的同桌小文说,“他挺怕他爸的。”
晚上8点,刘大海回家了。他的敲门声刚一响,正在闲聊的刘泽锴立即闭嘴,像支箭一样,安静而笔直地扎进自己的房间,钢琴声随即响了起来。
父亲也一样着急。进了屋,连衣服也顾不得换,直接走进琴房。
“压住!”刘大海声音很响,盖过门里的琴声,“太吵了!巴洛克音乐的特点是什么?!”
因为要准备去美国读书,刘大海还会特意和儿子说英文。
“我对现在国内的教育方式,学校给了孩子什么,还是有些意见的。”他说,他不想让儿子用整个初三,去学那些“对他往后人生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决定送他去美国读艺术高中。
尽管孩子足够优秀,但刘大海每次参加同学聚会,最后都演变成参加针对自己的“批斗会”。
“批得我抬不起头啊!”面相威严的刘大海少有地、露出无奈苦笑的表情,“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儿子不快乐。”
这位父亲在北方一个部队大院家庭严格的家教中长大。“对儿子能下这么大的功夫,或许有这个因素,我也不知道。”妻子陈喆说。
说起来,刘泽锴游泳,也是父亲带出来的。差不多5岁时,他弹好一遍曲子,就能得到一枚卡通贴纸,集齐10枚贴纸,就能“兑换”一次游泳的机会。
最初,这项奖励令刘泽锴无比喜悦。刘大海就为他找了教练,系统学习。
“我上当受骗了。”刘泽锴半开玩笑地说,小孩子的戏水很快变成周三、五、六、日每晚的训练,快乐又变成痛苦。
教练冯杰至今都记得那个光着脑袋的小胖子,年龄最小,却从来不哭。蝶泳是最需要刻苦训练的泳姿,但他听话极了,很快就在区里拿到分龄赛第一名,直到9岁那年,夺得全国冠军。
“很累,每次要游五六公里。”刘泽锴用银白色的笔,在一本黑色纸张的日记本上,写下潦草而简单的英文日记。实在不会的单词,就用拼音来代替。
每天的开头都是“今天我很开心”或者“今天我不开心”。大部分时候,他不论练琴还是游泳,总是“happy”的,但有一天,他游了好几个小时,写下了“我讨厌游泳”。还有一天,他出国参加活动,不用练琴,又写下“我很开心”。
这本日记里的主题,几乎只有钢琴和游泳。
“去游一会儿泳吧?”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母亲向刘泽锴提出。“能不能只游20分钟?”他央求道。
“我们只不过是把别人所谓的快乐童年,用来集中做一件事。”刘大海说,“我和孩子相辅相成,共同成长。”
他看不惯那些把孩子送来上钢琴课,自己今天“瑜伽”,明天“饭局”,或是在地下车库打瞌睡的家长,并和妻子约定,不坐在孩子身边陪课的,一律不教。
“你自己不付出,怎么让孩子去付出?”他反问道。
时钟指向晚上10点,刘泽锴从琴房里走出来,在房门边上站得笔直,隔着客厅,远远地对父亲说:“明天下午我能参加体能测试吗?老师说所有人都要去。”
“No way!”刘大海回答,毫不犹豫。刘泽锴“可是”、“可是”了两声,都被父亲的摆手打断了。他不再争辩,回身进屋。第二天是周四,按照惯例,他下午不能待在学校,要早早回家练琴。
时钟指向晚上11点26分,关紧的门里,刘泽锴指下的琴声,开始变得急促和易断,偶尔夹杂着错音。
“听,他开始烦躁了。”门外的父亲一脸了然地说。
在缝隙里努力做好玩儿的事
如果除掉所有的明星标签,刘泽锴就是一个普通的13岁男孩。
这天中午,他本趴在课桌上写作业,好朋友小元忽然冲上来攀住他的肩膀,两个男孩就在教室里你追我赶地玩儿了起来,一群男生跟着叫好。
维持秩序的班长小蓉气得小脸泛红,不客气地吼道:“你们俩给我坐下!”当被问及这个好动的刘泽锴平时表现如何时,小姑娘倒是给了积极的评价:“他很好相处,上课发言很积极!”
不在琴凳上的刘泽锴好动极了。他写作业时大脚趾跳来跳去,边走路边捂着嘴巴“动次打次”地玩儿B-BOX(一种流行的节奏口技)。他播放手机里最喜欢的欧美年度流行乐串烧,跟着摇头晃脑。刚听了一分钟,他又冲进屋搬出自己最近读的物理学著作,热情地谈论读后感。说话时手里还摆弄着个魔方,哗啦啦响,几十秒钟,6面完整呈现。
在被钢琴和游泳“切去整块”的时间缝隙里,这个少年努力做好玩儿的事:夜里装睡,偷偷读霍金的《时间简史》和玄幻小说《斗罗大陆》;吃饭时慢一点,多看会儿电视;上厕所时打一会儿手机游戏;给看美剧编排了“学英语计划”……
他喜欢披萨、汉堡和鸡腿,又对自己微胖的身材不满意。他不喜欢被叫做“钢琴王子”,讨厌表演时要画眉毛和眼线”。有人叫他的小名“叮当”,他会捂着眼睛害羞不爽。
他的微信朋友圈封面是和朗朗合奏的照片,但当同学说他是这位钢琴家的徒弟时,他干脆急了:“别瞎说,我和他没关系!”
在班主任龚刚的印象中,除了听话、成绩好,他也和同龄小男生动过两下手。因为精力旺盛,所以午休时候他管不住嘴巴,总爱聊天。
这个热爱理科的男生不喜欢语文课本,面对语文作业本上的C+,毫不在意。“中文就是个工具!”他说。因为早早就知道自己未来会去美国深造,所以他不愿意学中文、中国历史这些“以后没用的东西”。
被钢琴老师骂了,不少孩子会受不了,但他心态好得很:你批评吧,反正我也不会走。但最擅长的数学考砸了,他却偷偷抹眼泪。
他常常紧紧拥抱自己的班主任,说“老师我爱你!”被班长批评了,他笑着说“她的声音真好听!”同桌画了厚厚一本服装设计图,他觉得“太牛了,比我牛多了!”他爱开玩笑,打招呼时总是早上说晚安,晚上说good morning。
他还有个小小的秘密,属于心里一直喜欢的小姑娘。在手工课上,他制作了一只红色的叶脉书签,夹在一本《圣经》里,不敢送出去。
还有一次,他鼓足勇气想给漂亮的同桌小文来个击掌,手伸过去,发现小姑娘不理他,就乐呵呵地顺势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没有挫折可以击垮他。”游泳教练坚信。“我觉得他也有累的时候。”班主任说,“只是大多数时候,我看见他眼睛里全是阳光。”
他用一段长而费解的话来形容自由
“我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已经接近零点了,刘泽锴第三次走进客厅问父亲。
“半小时后。”刘大海说。小男孩一言不发,转头又进屋练琴。
尽管拥有配置还不错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和新款的智能手机,但他的家里没接通互联网。
他熟知不少电子游戏机的型号和游戏的名称,但都没玩儿过。看见别人手机上有游戏,他会满眼可怜地问:“能让我试试吗?”
和别的同学不一样,他害怕放假,盼望开学。
“放假就意味着铺天盖地的作业和钢琴。”刘泽锴说,他记忆中的每一个寒暑假都在练琴,“练到指甲盖翻起来,练到要爬着出门”。
“身心俱疲。”小男生用了一个大词,然后伸出十指认真数着“从小到大去过游乐场”,结果指头没用完,因为“只有6次”。
有些地方,包括香港著名的海洋公园,他甚至不认为自己去过,只说是“用脚踩过”。
“我们家没有春节元旦,永远在争取时间来练琴。”母亲陈喆坐在客厅里平静地说。
这位眼下供职于上市公司、业余教琴的母亲从不做饭,也不常在家。刘泽锴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小时候坐在琴凳左手边的那个人。
除了学琴这件事,陈喆和丈夫并没有在生活中让儿子依赖过。从小学开始,刘泽锴的晚饭,就是自己叫外卖解决,同学管他叫“吃外卖长大的孩子”。
父母忙于工作出差,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度过整个夜晚。爷爷奶奶来看他,见他一个人吃饭练琴,心疼得哭。
外公外婆来深圳小住,天天给他做一大桌菜。他连说:“你们来了,有饭吃了!”这句话让外婆难过不已。
他曾高票当选大队长,但没时间担任,只能去当文艺委员。最讽刺的是,“音乐”和“体育”,他曾考不及格,因为“一节课没上过”。
初一开学,他求父亲让自己参加军训。因为极为珍惜这个机会,他总是在训练时“直直地站着”,还拿到优秀标兵。
他喜欢漫画《父与子》,但父亲觉得漫画“毫无意义”,他经过恳求才得到一本。
当被问及喜不喜欢动画片时,他有点儿恼怒,一口回绝这个问题。“不喜欢!幼稚!不要问!”
对于房间里的乐高模型,他又忽然变得紧张起来:“嘘!千万别说出去。别人会觉得,你一个弹钢琴的,怎么还玩儿乐高呢?”
刘泽锴不知道什么是明信片,也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奥巴马之前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吧。”他答。
因为小学从三年级开始,他下午不到校上课,一度被同学排挤。
“四五年级那会儿,有一阵他看到钢琴就想吐。”同桌小文说,“他有时好好的,忽然就满眼泪水,上课还用圆规划自己,虽然不是那种真的划。”
在小文看来,熬过了那段时间,有了更多的收获,刘泽锴好了,而钢琴也真正成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学们都说崇拜和羡慕他。但说起这个话题,刘泽锴先是装作听不懂,然后用力揉着眼睛忍住泪水说:“怎么会有人羡慕我?”
在他脑海里,有过最疯狂的念头,是“哔一声,整个世界都消失”。他自认为最邪恶的念头则是,“有人拿着指挥棒一挥,所有人都变得跟我一样”。
他用一段长而费解的话来形容自由:当你的手臂变成“羽”,胸变成“长龙骨”,胸肌占身体30%~40%,骨头变成中空而且很轻——那就是自由。
“你听懂了吗?”这个男孩的眼睛直直地看过来,“我说的是鸟。”
“除非死,我不会不弹钢琴”
刘泽锴9岁时登上人生中第一场独奏音乐会的舞台,把准备了半年的十几首曲目演奏出来。
演出很成功,不少听众站起来为他鼓掌。那也是他第一次明白“掌声”的意义。
“但金牌不会让我开心,写篇论文也许会吧。”面对喝彩,他如今已经非常淡定,反倒充满热情地背诵了一遍“博士后”的定义,“麻省理工学院,你听说过吗?那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刘大海查到的数据,中国有大约5000万名琴童。
“这条路其实很窄,也很危险。”他说,“大多数学琴的孩子最终淹没在这个数字里。”
为之牺牲的并不仅仅是孩子。他和妻子的收入不算低,但都在本可以休息的时间里带钢琴和乐理课,他们的家只有简单的家具,没有任何奢侈摆设。墙壁是白白的,唯一的一幅装饰画挂在洗手池上,和音乐、艺术、大师没有半点关系。
刘泽锴在深圳上一堂钢琴课,花费1000多元,而在香港,这个数字是3500元——这个家庭的开支中,大部分被教育支出占据。
在刘泽锴弹琴的圈子里,有不少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Amy是陈喆的朋友,也是一位琴童的母亲。为了让女儿接受最好的钢琴教育,她不惜辞职到美国陪读。而她的丈夫则在国内“使劲儿”,赚钱支付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
“她的女儿对刘泽锴来说,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弹得特别好,但最近心理上有些逆反。”陈喆说,“这就很麻烦,一不小心就毁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放弃文化课。”
刘泽锴所在的南山外国语学校是深圳最好的学校之一。校方了解他的情况,会单独给些特殊的照顾,比如不用早读或不用上素质教育类的课程。
“真正到达顶峰的孩子,一定有天才。重要的是,如何发掘,不能让他被淹没。”副校长崔学鸿表示,“但不能让他孤立,还要培养他的合作精神。成功很快乐,但失去朋友就会不快乐。”
这位副校长见过不少“天才”,有的在音乐层面甚至展现出比刘泽锴更高的天赋和才能。但他更为在意的,则是那些被逼迫学琴的孩子,有的甚至不惜伤害自己,以摆脱钢琴。
刘大海不认为儿子是天才,“即使换一个孩子,只要按照教育他的流程再走一遍,也不会比他差。”
如今儿子即将赴美,夫妇二人没有选择陪读。
“将来就算他放弃钢琴学他喜欢的理科,我也尊重他。”父亲说。母亲补上一句,“其实他走了,我们也自由了。”
“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我理解我爸妈。”刘泽锴对此回应道。
2007年10月12日,深圳音乐厅落成后举办第一场音乐会,郎朗是剪彩和演出嘉宾。
花了100元,刘大海买了两张最便宜的门票,带儿子坐在离舞台最远的地方观看。
“我没想过有一天我儿子会登上那个舞台,因为那一天和我们当时坐的位置一样,太远了。”
那年,刘泽锴6岁,还是5000万名琴童之中普通的一个。
7年后,2014年8月23日,刘泽锴在这个“连针掉地上都能听到的”顶级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奏会,合作的是深圳爱乐乐团。
票卖得一张不剩,座位也几乎坐满,1200多张票根成了父亲的宝贝。
当时,因为担心,刘大海已经两天两夜吃不下饭了,而陈喆站在后台,紧张得连屏幕也不敢看。
那是一场极为成功的演出,刘泽锴自己也感到很满意。
“除非死,我不会不弹钢琴。”这个小男孩严肃地说,他也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只为一个人演奏,那一定是“to my girlfriend(给我的女朋友)”。
说起来,父亲刘大海的梦想是“在老泪纵横中为儿子鼓掌”。但儿子刘泽锴多年来的梦想,仅仅是学会骑自行车。因为需要保护双手,他从没机会学,直到前不久一家电视台来采访,他才赶紧趁机说出了这个愿望。
至于他最想要当的科学家,“如果真的没机会,那就算了。”他迅速说。
在深圳一个秋天的夜晚,刘泽锴游完泳,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蹬上自行车。他刚学会骑车,动作还有些笨拙。陈喆开着轿车跟在他身后,眼睛一秒也不敢放松。
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黄灯亮了。就在陈喆不得不停下来的几秒钟之内,刘泽锴突然加速踩动脚蹬,消失在母亲的视线中。
责任编辑:wb001
文章来源:http://edu.72177.com/2014/1113/1886851.shtml